- 近期网站停站换新具体说明
- 按以上说明时间,延期一周至网站时间26-27左右。具体实施前两天会在此提前通知具体实施时间
主题:【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系列终结篇) -- 思炎
思炎对几十年的喉舌宣传情有独锺,老是抄这种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编剧,真不晓得是为了什麽。
就如这里说什麽美军选择不遣返战俘听取美军解释,根本是狗屁。当时志愿军俘管怕这23名美军改变主意,在他们里面搞小组织、搞集体行动,不让他们去一个个地听取解释,还要他们绑架印度军官进行斗争,跟张泽石等亲共战俘在战俘营里搞的那套如出一辙。
像你上面说的什麽美军战俘听取解释云云,只能骗自己人民,骗不了外人。像这里这个俘管的也在睁眼说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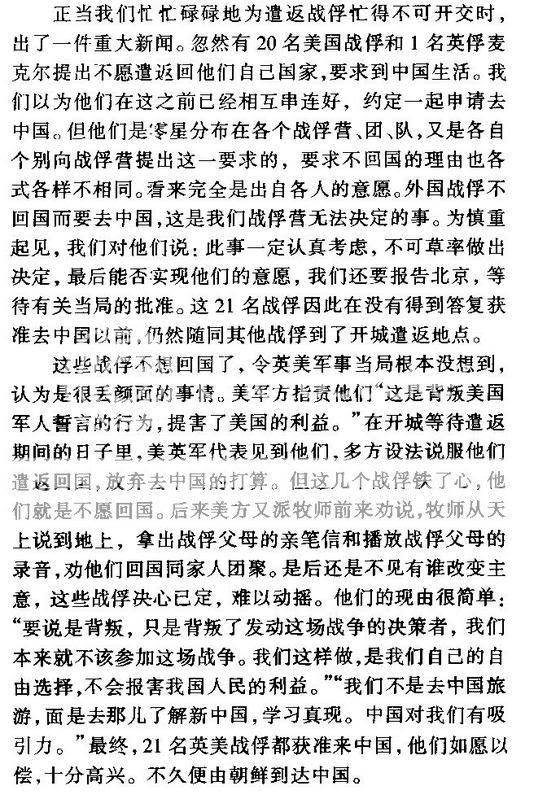
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23名美军战俘集体行动,但其中两个人还翻墙逃跑,让志愿军俘管更不放心,透过潜伏在解释区中遣会医院里的俘管领导指示,根本没让他们去解释营帐逐一听取解释。这里是後来留下来的21名战俘之一的回忆录,自己看:
Morris R. Wills: Turncoat, An American's 12 Years in Communist China, Prentice-Hi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6
投奔(Defection)
1953年8月6日,战俘营的指导员叫我过去,说我下午要调到5号营;这时5号营的战俘已经遣返完毕,我们看到他们坐卡车路过我们营地。指导员甚至不让我回去拿东西,他把我的行李带了过来,怕有人对我不利或者攻击我。这时已经是最後阶段,营里有些人已经表明态度不想回国,(营里)一般都认为他们是叛逃。
我想你可以叫我投奔者(defector)或改换阵营者(turncoat),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变节者(deserter)或叛徒(traitor),因为美国和中国人签署过协议,如果想要的话,我有权利到中国去。根据这个,我就不是叛徒。再说,我的待遇也不好,我们被扔在这里,被外界完全遗忘。他们显然没有尽力要让我们重获自由,他们遗弃我们,把我们留在这里整整两年,自己却在国内过好日子。
那时候,经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训练后,我心目中并不认为自己在叛逃。我认为自己仍是美国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另一种方式来帮助美国,也许以后我能帮助改变体制,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当然,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一点也不。
1号营中我们连里只有另外一人也来到中国──和我同一天被俘的上等兵Richard R. Tenneson。即使是他,也是直到在营司令部见面时才知道我要去中国。还有其他更多人本来应该也要去中国,但是中国人行事非常隐秘,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谁要去中国。我们连里应该还有另外4到5个人,而1号营5个连中应该可能有多至25人要去。
我必须和连指导员面谈,他想确认我不会改变主意。他说我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多的物质条件,我必须准备过着物质条件较少的生活。我告诉他说我知道中国很穷,生活条件没有美国那么好,但这对我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接着我们被带往营司令部,之后Tenneson和其他连的许多人也陆陆续续过来。他们把Tenneson、我及另外三个人送上一辆敞蓬俄国卡车。日後那三个人被中国人刷下来。Tenneson和我一样也经历了转变的过程,但他在战俘营中非常敢言,给他招惹了很多麻烦,有一两次其他人试图在晚上修理他。我以前一直避免被人看到和他在一起。
吃完午饭后我们离开1号营,卡车上没有卫兵,只有前面开车的中国司机。现在是我们第一次获得信任——完全的信任。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在鸭绿江南岸的5号营。你可以看到对岸的中国。一些中国指导员在等我们,这是他们第一次称我们“同志”。
我们见到了从3,4,5号营过来决定留下的人,他们互相称“同志”(2号营是军官营)。我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来决定哪些人我喜欢,哪些人不喜欢。有三四个我根本懒得搭理──都是喜欢自吹自擂之辈,我拿定主意要跟另外一些人保持距离。这里总共有27人:21个美国人后来去了中国,另一个苏格兰人Andrew Condron,原来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以及五个后来没去成的。
两个中国人担任我们的教官,一个姓田,资深红军政委,一个秃头老头戴一副眼镜,至少六十多了。另一个姓张,是他的下属。他们和优异的翻译一起过来,马上把我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密的群组,进行有系统地训练。当时我并没有觉查到,但是现在回顾的话,这是一道程序让他们来判定哪些人能坚持挺过停战协定中规定在中立区停留的三个月。他们要尽力找出我们中间是否有人是被送进来搞破坏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要剖析自己,并被其他人所剖析以决定他是否合格能不遣返,是否能挺过三个月的时间、保持对组织的忠诚?
我们开始按照被教授的方式来开批评会。每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解释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被遣返,那些在战俘营里的旧识必须要提出对他的看法。每次两个中国教官都在场,来确认每个人是否诚实。我们也选了组长,上士 Claude Batchelor和军士 Richard G. Corden被选为正副组长。
后来,那三个月解释期过了之后,这两个中国教官告诉我们当时对每个人的评价。我被认为是一个相当保守、平静的人,应该可以挺过这三个月,不会替组织惹麻烦,也不会改变主意。他们把我的成分划成“富农”,因为从我的自传中得知,我父亲有175英亩土地。这在美国不算什么,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相当于超过一千亩土地——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因为我父亲没有雇工,他没有被划为地主,他被认为是“富农”。因为我是他儿子,所以我自然也是划为同一种成分。每个人都必须被划进某种成分里。
然而,习惯上,中国人总要拿些人树立榜样。他们发现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从1号营中来的,曾经和朝鲜人做过大麻买卖。中国人在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田教官宣读了对这三个人的指控。到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感觉自己非常的“进步”,认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每个人都是同志,也应该表现的像个“同志”那样。中国人暗示这三人都是被派过来搞破坏的,鼓励其他人起来对这三人进行批判。他们一步一步的上纲上线直到那三个中有人眼泪都下来了——开始啜泣起来。最后,正如中国人期望的那样,这三人改变了主意,“自愿”要求被遣返。中国人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对他们说他们还是“和平战士”,并且希望他们回到美国后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作斗争。
在5号营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是社会主义圈子中的一员,和这个组织中的其他人关系密切。我认为我应该尽我所能对这个组织中的所有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帮助。我认为自己是个和平斗士,想尽我所能在这个世界上争取和平。我觉得社会主义,以及最终的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些强烈的感觉源于我在1 号营的学习经历。虽然我当时并不觉得,但你可能要说我当时是被洗脑了。
在5号营我们被教导要维持组织的团结,要有对组织领导的责任感。中国人让我们相信这是一场我们必须面对的斗争,只有“英雄”、佼佼者,才能挺过中立区的解释阶段。
我们在中立区的三个月将受印度军队管辖。我们将完全靠自己;理论上不会和中国人有任何联系。美国陆军的“解释人员”理论上应该有机会对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回国。因此,我们在五号营进行了模拟训练对付这些解释人员。我们被命令在面对解释人员时要制造麻烦,让他们解释不下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唱歌,制造噪音,把背转过去──任何可以不听取解释的事情。我们应该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美国是战争贩子。
这时我还不知道,但中国人在我们组织里又设立了另一个组织,在这个核心组织中有 Batcherlor,Corden,Sullivan。他们和这核心组织安排了一套灯光密码,以便与在中立区的我们直接联络。灯光信号在夜间用过几次。他们也试图训练我们的吉祥物,叫Nonrept的小杂种犬,来传递信息,但没有成功。张教官还计划把头剃光、混进营里的医院里面做苦力。我本来不知道这事,但三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我去医院补牙,发现他在那里,他叫我别声张出去。
在我们前往中立区的前夕,中国人为我们办了一个酒菜丰沛的盛大宴会。我们开怀畅饮,中国人也一样,有一些人不得不被抬着回去;有个家伙甚至他自己的床烧掉了。像这样的活动一是为了把我们团结起来、巩固组织,二是为了让我们的情绪充分发泄。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送上卡车,开了两天才到中立区附近的开城,沿途土路又窄又崎岖,我身体还从来没有这么酸痛过。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营区里一个星期,并且被安排到一个显然以前是富人专用的漂亮朝鲜澡堂洗澡。我们又开了很多次会,准备如何应付解释人员。如果有人表现落伍的话——例如对性感兴趣——他就会被别人告发。所有事情在中国都是以这种方式极有效地掌控,你总是隶属於某个组织的一部份,假如这个组织有二十个人,其他十九个就会持续监视你,你也要持续监视其他人。任何事都必须汇报,否则的话你将被人告发你不汇报,你不得不照着做。这就是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四分五裂的原因,也是人民为何还没有起来反抗的原因。
在中立区我们被安置在一处特别营区内,在一个小山上,大约两英亩见方,周围被铁丝网环绕。这是我们被俘后第一次住在铁丝网里。远远望到这个营区我们就开始唱歌,印度人就在那里,还可以看见一些美国军官。我记得那里有一些美国司机聚在一起,当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唱美国国歌,他们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因为不记得歌词,我们这边就大笑、喝倒彩。
我们被安排到营房里安顿下来。慢慢地,组织里的成员一个接着一个地到铁丝网围绕着的医院去,并且呆在那里不回来,最后只有八到九个人留在营房里。当时我还不知道张教官就在医院里,并且直接控制着那里的人。解释期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组织内部的那个核心组织。我并不介意有个核心组织,但是却不太高兴自己不知情,我对有些人更受信任感到反感。这造成意见不合,我们的组织现在开始有裂痕了。
组织里有两个人最後决定还是回国。一个是Edward S. Dickenson 上士,他就睡我旁边,晚上的时候常常弹吉他,我们一起坐着唱歌。他假装头痛乘隙溜走了。另一个是Batchelor,中国人认为他是5号营里最“进步”的人,在他们的指引下,Batchelor被选上担任组长。他人非常好,非常真诚,但就在待在中立区快结束的时候,他收到了日本妻子的一封信,当天午夜他就走了。
我确曾几次思考过自己的决定,但是我很固执,我在战俘营就已经拿定主意,不会轻易改变。我决定不让这件事情困扰,不要再多想了。
我们一直对印度人找麻烦,抗议他们的牙医试图影响我们,抗议给我们送来圣经。中国人也命令我们绑架营区的印度指挥官,以迫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派人过来听取我们的抗议。我们对此争议很大,我是几个反对的人之一,我认为这相当愚蠢。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来自中国人的命令。最后,Batchelor取得了大多数的支持,我也不得不同意一起行动。
组里一些人把那个军官骗到我们的营房中,不让他出来。当我们抓到他後,印度人就在营房外围架设机枪,并且开了一辆坦克过来。中立国委员会几个小时之后才有人过来,最后我们呈递了请愿书之后把那印度人放了。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去见解释人员,由於中国人的阻挠,整个解释程序无法进行。在我们到中立区大约两个月以后,我们被转运到另一个营区,非常小,因为形状就像香蕉,我们叫它香蕉营。至少有一天,美国人开车载过来一个扩音器,宣布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他们没有威胁我们,只是给我们了一个最后期限——我记得大约是五分钟。
我们已经对这种事情有了准备,我们都不去听广播,因为,一旦你开始听,你就会开始想,你就开始动摇起来想回国了。对我而言,这样做不仅仅是违背我对我组织的诺言,也是背弃我自己的决定,即背弃我自己。
那些美国人等了大概五分钟,看到没人出来,他们就拿下扩音器离开了。
这时我们组织里已经有了很严重的意见冲突,我们已经厌倦了集体生活,而那时我们也没有和早先一样地被严格控制。当Batchelor走的时候,我们组织就分裂了。简直不可想象一个组的组长会走,他从来都是最受信任的,并且一直努力保持组织的团结。我们对他更觉得难过而不是愤怒,每个人都喜欢他。我们认为他会入狱,实际上也是如此。
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营门洞开,并且见不到一个人。印度士兵已经走了,中国人过来接管,张教官也从医院过来。我们又在营里面住了几天,接受两个亲共记者 Alan Winnington和 Wilfred Burchett的采访。中国人同意在平壤举行一场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又花了几天的时间来训练——可能会问什么问题,以及怎么回答。我们要强调麦卡锡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和平。Corden现在是组长,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从1946年就就在美国陆军当兵,也是我们这群人中智商最高的。他发表了一通演讲,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回答了问题,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我们预期的那些。
之后,我们就准备去中国了——二十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海军陆战队。组织中的一些人想去苏联而不是中国,但中国人和他们个别谈话,说服他们都去中国。接着田教官宣读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接受我们作为自由的美国公民到中国去。又开了一个宴会,我们和中国人都喝醉了。
我们在开城呆了几天时间,订做平民服饰,在城里面转转并且四处观光。他们为我们弄了一列特别列车——车头,两节车厢,以及两节装载我们的俄国吉普的平板车。我们穿过朝鲜,看到了平壤的废墟,没有一栋房子还立着,人们都生活在山洞里。中国摄影师上车为我们拍照。1954年2月24日早晨大约4点钟的时候我们跨过了鸭绿江到中国境内。我从窗户望出去,外面雾蒙蒙的又冷——非常黑,非常灰暗,非常冷。
- 相关回复 上下关系8
压缩 4 层
🙂历史实情?咱看几个去台湾的战俘几十年后的回忆. 8 flyingcatgm 字2978 2010-04-15 06:43:20
🙂我不看那种马路货的报纸 Light 字5147 2010-04-15 04:01:42
🙂故作高深,还继续表演这套低级的把戏 8 思炎 字13526 2010-04-15 06:14:17
🙂老是抄喉舌宣传,你累不累啊?

🙂阁下贼喊捉贼,面不改色心不跳,佩服 夜月空山 字0 2010-05-18 19:00:03
🙂你是抄谁的 沧溟之水 字0 2010-04-16 18:15:37
🙂对比美国如此卑鄙无耻的对待志愿军被俘人员, 8 思炎 字1018 2010-04-15 15:31:49
🙂两方交战,让第三方来甄别也是国际公约的规则吧? 非真 字54 2010-04-14 21:3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