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网站停站换新具体说明
- 按以上说明时间,延期一周至网站时间26-27左右。具体实施前两天会在此提前通知具体实施时间
主题:《左传》中的成语05 -- 桥上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桓十五年传》(p 0143)(02150201))(017)
有一句成语叫“人尽可夫”(rén jìn kě fū),不是什么好话,就出自这里。不过这里的雍姬(祭仲女儿)也糊涂,丈夫奉了国君的指令要杀自己父亲,她竟去问她妈,还是这么个问法,于是她妈就为了自己的丈夫牺牲了女儿的丈夫,理由还这么奇怪,所以郑厉公才会愤愤不平:“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尽管有聪明睿智的妇女,但就像有无脑的男人一样,也有糊涂的女子。
但是从语义本身来说,“人尽夫也”和“人尽可夫”并不一样,“人尽夫也”反映的是当时还没有后来的贞操观念,是个正面的话,所以祭仲的老婆才会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左传》中就有几个例子说明当时的贵族是不在乎女子再嫁的,也许是因为当时漂亮的女子很少吧: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偪(bī)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文六年传》(p 0550)(06060501))(048、054)
这一段提到的辰嬴又叫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当初晋怀公在秦国作质子,秦穆公曾把怀嬴送给晋怀公当老婆,同时负责监视晋怀公。晋怀公逃回晋国,她没跟着,所以后来她又被秦穆公送给了晋怀公的叔叔晋文公当副老婆,改叫辰嬴,最后在晋文公夫人里排位第九。
此时这些晋国的大夫就在讨论究竟是辰嬴的儿子公子乐当国君好还是杜祁的儿子公子雍当国君好。但辰嬴为两任国君所喜爱(嬖于二君)甚至可能成为长处,由此可见当时的贵族未必在乎贵族女子再嫁。
而且这位辰嬴(怀嬴)本人也没因再嫁把自己看低了,她在晋文公和文嬴的洞房花烛夜还把晋文公(当时的公子重耳)训得一楞一楞的: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僖二十三年传》(p 0410)(05230608))(038)。
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宣十五年传》(p 0764)(07150502))(057)
这一段是《左传》中讲的著名的“结草”故事,其中魏武子的儿子魏颗在魏武子死后将他父亲的“嬖妾”嫁了出去,结果得了好报,鬼神帮助他立下了重大战功。可见当时贵族们的主流思想未必要求妇女在丈夫死后守节。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成十一年传》(p 0852)(08110301))(080)
但是当事摊到自己头上时,也很难无动于衷,这里的施孝叔虽然娶了管于奚的寡妇,但又被夺走给了势力更大的晋国重臣郤犨,等郤犨被杀,郤家垮了台,晋人又把这个寡妇还给施孝叔,此时施孝叔憋着的一股邪火就发在了这位寡妇的(和郤犨生的)两个孩子身上,他把这两个孩子都给扔黄河里了。这可能也反映对妇女贞节的要求来源于对后代血缘纯洁性的要求。
但这个寡妇的同母异父哥哥(子叔婴齐,谥声伯,鲁卿)势力大,她干脆就回了娘家。这也算是“人尽夫也”的一个注脚吧——只要娘家厉害,“夫”可有可无。
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公孙明知叔孙于齐,归,未逆国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长而后使逆之。(《昭四年传》(p 1257)(10040802))(091)
这一段省略了主语,其实说的是鲁国的叔孙豹(穆叔),他是家里的老二,没有职位可以继承,只好到齐国去找出路。此时由于他哥哥犯了事,但他的家族势力还在,所以“鲁人召之”,让他回鲁国继承族长的位子以及他家在鲁国的世职。
他本来在齐国已经娶了“国”家的女儿“国姜”,但他急于回国抢位子,就没带着“国姜”一起回国,哪想到几天的工夫“国姜”竟又被他的好朋友公孙明(子明)娶了去,叔孙豹一生气,就把自己和“国姜”生的俩儿子扔在了齐国。尽管俩儿子长大以后又被他接了回来,但他还是心有芥蒂,终于中了他另一个儿子、私生子竖牛的挑拨,酿成悲剧:
田于丘莸(yóu),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杜洩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寘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四年传》(p 1257)(10040803))(091)
在叔孙豹生了重病以后,竖牛骗他说“孟”(叔孙豹和“国姜”的儿子)见了“国姜”的使者(即“北妇人之客”),触动了叔孙豹内心的嫉妒,竟把“孟”杀了,又赶走了他和“国姜”生的另一个儿子“仲”,结果叔孙豹自己竟被竖牛给活活饿死了。这里尽管有各种嫉妒,但这里重点还是说叔孙豹怀疑儿子的血统,而对“国姜”再嫁本身则未置一词,也反映了当时的贵族们对这件事并不看重。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bì),不获其尸。其子黑要(yāo腰)烝(zhēng)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yīng)父,成公之嬖(bì)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xū),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成二年传》(p 0803)(08020601))(068)。
还有上面这个著名的夏姬,尽管嫁了这么多人,还“克”死了这么多人,但她太漂亮了,巫臣最后还是明媒正娶了她。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襄十五年传》(p 1024)(09150901))(089)
这一段的背景是“堵”家的人参加了“西宫之乱”,受到惩罚,地位降低,郑国的执政者为了避免当时霸主晋国的重卿范氏家介入,就把嫁给“堵”家堵狗的范氏家的某个女儿送回了娘家。可见范氏家并不很在乎让自家的女儿再嫁,只在乎女婿的地位,反正“人尽夫也”。
当然这只是不计较妇女再嫁,其实当时的妇女已经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才有以下种种说法:
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而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庄二十四年传》(p 0229)(03240201))(026)。这是说根据“礼”,男子在各方面都要高于妇女,而且要强调出差别来,这是“国之大节”。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001001)。史曰:“是谓《艮》之《随》 (100110)。《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襄九年传》(p 0964)(09090301))(070)。这里已经把妇女“固在下位”了。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僖元年传》(p 0279)(05010701))(026)。这里明确提出了“女子,从人者也”。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chāo chéng)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昭元年传》(p 1211)(10010701))(111)。至于这里的“夫夫妇妇,所谓顺也”,当然说的是老婆要“顺”着丈夫。
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庄十四年传》(p 0198)(03140301))(025)。这里作为男子的楚文王自己还没怎么样,息妫倒说出“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这样的话,不过这些话在我看来其实是息妫没法直接指斥楚文王而发的怨言,而她怨言的重点其实在于楚文王是她的杀夫仇人而她不得不“事”。但是这些话却被后来的一些人强调成为不能“事二夫”,应该是歪曲了息妫内心的意思。
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踰阈,戎事不迩女器。”(《僖二十二年传》(p 0399)(05220901))(043)。但是当时为保持血统纯正所采取的措施却越来越严格了,上面这一段已经要求贵族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兄弟都不能随便见了。当然对于当时的贵族来说,兄弟是危险的亲。
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定五年传》(p 1553)(11050702))(110)。这里“为女子”就应该“远丈夫”也是为保持血统纯正所进行的教育,不过季芈说出来恐怕就只是借口而已了。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成二年传》(p 0795)(08020306))(069)。这一段也反映当时的妇女还是把父亲放在丈夫头里,以自己的娘家为重,只要父亲没事,丈夫就不用问了,这里父亲和丈夫一个是“锐司徒”,一个是“辟司徒”,地位差不多。可见当时对于女子来说,娘家家族非常重要,还没有完全“出家从夫”,而是出了家还可能“从父”。在这样的逻辑下,当然是“人尽夫也”了。
就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也才有秦赢放走秦国的战俘、许穆夫人要帮助卫国复国这样的事。也才有下面郑-大子忽是否该娶齐国公主的纠结以及宋国因雍氏家族插手郑国内政的情形。
————————————————————
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一些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隐五年传》: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p 0045)(01050401))(017)
我的粗译:
这年四月,郑人进军卫国的放牧地,报复上年宋、陈、蔡、卫四国军队包围郑国东门五天的战役。反过来,卫人又请了燕师(南燕)一起讨伐郑国。郑国的祭足、原繁、洩驾三人率领三军在燕师的前方拦住其去路,又派曼伯与子元两位公子悄悄带领制邑来的部队(制人)从后方袭击燕师。燕人对自己眼前的郑国三军的动向很注意,却没有提防从后面来的制人。到了六月,郑国的两位公子率领的制人在北制打败了燕师。贵族们总结说:“要不能防备意外,就不能带兵。”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原认为曼伯是大子忽、即后来的郑昭公,后认为曼伯是子仪。主要根据是《昭十一年传》有云“郑-京、栎实杀曼伯”((p 1327)(10111001))(108、109),而且此事与大子忽(公子忽)为高渠弥所杀之情形不符。
但我觉得大子忽(公子忽)为高渠弥所杀之细节今已不知,但据曼伯以伯为字,且于此处及《桓五年传》中两次出现均位在前、此次更在公子之前看来,此人不太可能是庄公或昭公之弟,或可能为庄公或昭公之庶兄,否则还是以之为大子忽(公子忽)更合理(“曼”字与“忽”字的意义亦可有关联)。
又,“郑-京、栎实杀曼伯”之“曼伯”还可能为“檀伯”之误,《桓十五年传》:“郑伯因栎人杀檀伯”((p 0143)(02150601))(017)与“郑-京、栎实杀曼伯”颇有相似之处,“曼”字与“檀”字的读音亦有接近之处。
子元则是大子忽之弟公子突、后来的郑厉公。
下面是我估计的各相关地点的位置以及截自《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的、包含南燕、郑、卫、北制等地点的地图:
南燕:东经114.37,北纬35.25(延津县司寨乡大城村南古胙城)。
郑: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北制(制,虎牢):东经113.20,北纬34.85(汜水镇虎牢关村)。
卫(朝歌):东经114.19,北纬35.61(淇县摘星台周围)。

————————————————————
《隐七年传》: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p 0055)(01070701))(017)
我的粗译:
郑国的公子忽在周天子那里作质子,被陈桓公看上了,要让他当自己的女婿,郑庄公同意了,定下了这桩婚事。
《隐八年传》: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p 0058)(01080401))(017)
我的粗译:
第二年四月甲辰,公子忽自己前往陈国迎娶妫“姓”的老婆。七天以后,辛亥这天,带了妫氏回国。又三天以后,到甲寅这天,回到了郑国。陈国派了大夫陈鍼子送亲。公子忽没等祭告祖宗就和妫氏睡到了一起。于是陈鍼子批评道:“这么干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夫妇,欺瞒了祖先,违背了‘礼’,不会长久。”
一些补充:
陈国:东经114.88,北纬33.74(淮阳县城)。郑国与陈国当时直线距离一百三十公里左右,由于地处平原,实际里程大概接近三百里,路上大概走了四天,还是挺快的。
下面是这些天的干支排序: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
————————————————————
《隐九年传》:
北戎侵郑。郑伯禦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p 0065)(01090601))(017)
我的粗译:
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兵抵抗,但对如何应付没把握,就和身边的人商量说:“他们是徒兵,我们是车兵,就怕他们不断偷袭我们。”这时公子突建议说:“可以派一些勇敢又灵活的人,和那些贼人接触以后就赶快逃走,主上事先设下三道埋伏等着。这些戎人轻率而没有纪律,贪心又不团结,打胜了互不相让,打败了也不肯互相救援;在前面的人看到有便宜可占,一定会拼命追赶,等碰到埋伏,又会赶紧逃跑;后面的人又不会救援他们,他们只能垮下去了。这样我们就能战胜他们。”郑庄公采纳了他的建议。
《隐九年传》: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p 0066)(01090602))(017)
我的粗译:
追在前面的戎人遇到埋伏后果然立刻转身逃跑,祝聃领兵追击他们,三路伏兵齐出,把戎师截成几段,前后夹击,彻底消灭了这部分戎师。其余的戎师拼命逃走了。十一月甲寅这天,郑人大败戎师。
————————————————————
《桓六年传》:
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p 0113)(02060401))(017)
我的粗译:
七年以后,北戎又侵犯齐国,齐国派人请求郑国出兵,郑国由大子忽领兵救援。这年六月,大败戎师,杀掉了戎人的两名将领大良和少良,还有三百名甲士,并将这些首级献给了齐国。
《桓六年传》:
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餼,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p 0113)(02060402))(017)
我的粗译:
当时有好几家诸侯的军队一起来帮助保卫齐国,齐人要向这些军队馈赠食物,请我们鲁国排一个次序,结果我们鲁国把郑国排在了后面。郑忽认为自己立了大功,不应排在后面,生气了,所以后来郑国又派兵进攻我们鲁国,在“郎”那里打了一仗。
一些补充:
郑忽即大子忽,这是“国”名和“氏”名当时用法类似的一个例子。
北戎来侵,各家诸侯都来救援,反映当时各家诸侯的同仇敌忾,这一仗也是农耕族与游牧族斗争的一部分。
“郎”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5.13(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乃离曲阜较近之“郎”,杨先生于《隐元年传》注云“当在今鱼台县旧治东北十里”(01010301)的“郎”,则是离曲阜较远之另一“郎”:东经116.5,北纬35.0(鱼台县旧城里村西))。
《桓六年传》:
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p 0113)(02060403))(014、017)
我的粗译:
当初我们桓公还没从齐国娶回文姜夫人之前,齐僖公曾经想把文姜嫁给郑-大子忽,但他推辞了。有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各人有各人相配的对象,齐国太大,我配不上。《诗》里说了:‘自求多福。’我的前途由我自己决定,为什么要依傍大国?”贵族们都认为他“善自为谋”。等这次他打败戎师以后,齐僖公又提出要把别的女儿嫁给他,他还是坚决推辞了。又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次他回答说:“就算没为齐国出兵,我已经不敢沾齐国的公主了。这回奉了主上的命令为齐国救急,完了带个老婆回去,就成了出兵为自己讨老婆,‘民’会怎么说我呢?”于是他通过郑庄公坚持推掉了这门亲事。
一些补充:
这一段《左传》产生了“齐大非偶”(qí dà fēi ǒu)这个成语,这个成语现在不太常用,但用法和这里的原意差别不大。另外“自求多福”(zì qiú duō fú)也是现在的成语,不过原始出处是《诗经》;而且:原意是说给自己,是自励;现在则变成说别人,是事不关己的观望(甚至可以是恶意的,例如多福斋)。还有“善自为谋”(shàn zì wéi móu),应该也是成语,但不太常用。
————————————————————
《桓十年经》:
秋,公会卫侯于桃丘,弗遇。((p 0127)(02100003))(017)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p 0127)(02100004))(017)
《桓十年传》:
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p 0128)(02100501))(017)
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p 0128)(02100502))(017)
我的粗译:
上次救援齐国四年以后的冬天,齐国、卫国、郑国来讨伐我国,在“郎”打了一仗,这事其实我们有理:
当初北戎为患齐国,各家诸侯都来救援。郑国援军的主将公子忽立了大功。齐国慰劳各家的部队,请我们鲁国排座次,我们鲁国按照周王朝的位次把郑国排在了后面。郑人生气了,来进攻我们,并向齐国请求派援兵,齐人则拉来了卫国的兵。因此这算不上“侵伐”。至于《春秋经》上把齐和卫写在前头,则是按照周天子那里的“班爵”。
一些补充:
这年秋天鲁桓公去桃丘会见卫宣公,结果卫宣公背约不来,就预示了他们要来讨伐鲁国。这次郑国为小事就纠集了两家诸侯来讨伐鲁国。也反映当时郑国的强大,连太子都这么威风。
“桃丘”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1,北纬36.1(山东阳谷县陶城铺、河南台前县徐固堆附近)。此处的“郎”当为离曲阜较近之“郎”,推测位置为:东经116.93,北纬35.13(鱼台县前后郁郎村周围)。
“故不称侵伐”是解释《春秋经》为何写“来战于郎”而不写“侵我”或“伐我”。我推测,利用《左传》讲解《春秋经》的人很可能在讲解时手上就拿着《春秋经》的相关竹简,所以在很多条《左传》中才会很具体地解说相关《春秋经》的写作意图。
《桓十一年经》: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p 0129)(02110001))(017)
《桓十一年传》:
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p 0130)(02110101))(017)
我的粗译:
下一年,齐、卫、郑、宋四国又在“恶曹”盟会。
一些补充:
“恶曹”据说就是“乌巢”,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4.13(延津县东南僧固乡史固村一带)。
————————————————————
《桓十一年传》:
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从。((p 0131)(02110301))(017)
我的粗译:
后来的郑昭公(当时是大子忽)打败北戎那回,齐人要嫁给他另一位公主,他推辞了。祭仲劝他:“你一定得娶她。咱们主上宠爱那么多女子,你又没有强大外援,怕接不了位。三位公子都可能当国君。”但大子忽不肯听祭仲的。
一些补充:
当时贵族女子出嫁以后,有不少仍然还心向原来的“氏”族(包括诸侯国),而且也会得到原来“氏”族(包括诸侯国)的支持。
《桓十一年经》: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p 0129)(02110002))(017)
《桓十一年传》:
夏,郑庄公卒。((p 0132)(02110302))(024、017)
《桓十一年经》:
秋七月,葬郑庄公。((p 0129)(02110003))(017)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郑庄公去世了。
《桓十一年经》: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p 0129)(02110004))(017)
《桓十一年传》: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p 0132)(02110303))(017)
秋九月丁亥,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p 0132)(02110304))(017)
我的粗译:
当初,“祭”地的长官“仲-足”(即前面的祭仲,这里的“足”应该是此人的“名”,而“仲”则是此人的“字”,同时也是行次)有宠于庄公,庄公让他当卿。他为庄公娶了鄧曼,鄧曼生了后来的郑昭公。所以祭仲拥立了昭公。宋国的雍氏家族也有女儿嫁给了郑庄公,叫做雍姞,她生了后来的郑厉公。雍氏家族受人尊敬,还有宠于宋庄公,所以宋人把祭仲引出来抓住,对他说:“你要是不立‘突’就杀了你(“突”即前面的公子突,后来的郑厉公)。”他们还把后来的郑厉公抓了来,要求厉公以后回报他们。于是祭仲与宋人举行了盟誓,带着厉公回国立为郑国国君。
这年秋九月丁亥,郑昭公逃往卫国,十二天以后,己亥这天,厉公继位为君。
一些补充:
此处《左传》专言祭仲为祭封人,说明祭并非其“氏”。前面《隐元年传》中就有同为郑国人的“颍考叔为颍谷封人”((p 0014)(01010406)),其中的颍谷显然并非颍考叔的采邑。另外《论语》中之“仪封人”与《庄子》中之“长梧封人”亦分别指“仪”和“长梧”两邑的长官而非该两邑的封君。
当时能有“氏”并不是简单的事,祭仲虽然后来当上了卿,但也未能挣到“氏”。当然这是在春秋前期,到春秋后期,得“氏”的家族逐渐多了起来。
《桓十三年经》: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p 0135)(02130001))(017)
《桓十三年传》:
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后也。((p 0138)(02130301))(008、017)
我的粗译:
宋国因其在拥立郑厉公中起了关键作用,所以不断向郑国索要好处,郑国受不了了,所以约集了纪国、我们鲁国以及齐国,与宋国、卫国、南燕国作战。《春秋经》中没提到这一仗是在哪儿打的,是因为我们鲁国的军队去晚了没赶上。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桓十五年经》: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p 0141)(02150004))(017)
《桓十五年传》:
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壻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p 0143)(02150201))(017)
我的粗译:
祭仲专权,郑厉公受不了了,就要祭仲的女婿雍纠杀掉祭仲。雍纠约了祭仲在郊外享宴,雍纠老婆(也是祭仲的女儿)雍姬闻出点味儿来,就去问她母亲:“父与夫孰亲?”她是问爸爸和丈夫谁亲?她母亲告诉她:“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这是说人人都可以当丈夫,可父亲只有一个,怎能比得上?于是这位雍姬就去告诉祭仲说:“雍氏不在自己家里宴请您,却要到郊外去,我觉得有点奇怪,所以跟您说一声。”结果祭仲杀了雍纠,把他的尸首扔到了周氏之汪。郑厉公收敛了他的尸首放在车上逃走,路上对手下埋怨雍纠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年夏天,郑厉公流亡到了蔡国。
一些补充:
这位雍纠非姬姓,很可能来自郑厉公的母家宋国的雍氏家(姞姓),是郑厉公从宋国带回来的亲信,在郑国没有根。也因此郑厉公才会将他的尸首“载以出”。
蔡国推测位置为:东经114.25,北纬33.25(上蔡西南卢岗乡翟村东二郎台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遗址城墙长度(米):东2490,西3187,南2700,北2113)。
《桓十五年经》: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p 0141)(02150005))(017)
《桓十五年传》:
六月乙亥,昭公入。((p 0143)(02150301))(017)
我的粗译:
当年的六月乙亥这天,郑昭公又回到郑国。
《桓十五年经》: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p 0142)(02150009))(017)
《桓十五年传》:
秋,郑伯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p 0143)(02150601))(017)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郑厉公联络栎人杀掉檀伯,占据了郑国的“栎”这座城。
一些补充:
《春秋经》仍然称郑厉公为郑伯,表明周王室和鲁国此时的态度。
“栎”推测位置为:东经113.47,北纬34.16(“栎”即“历”,约等于禹县老城,近方形城,城墙长度(米):东1600,西1750,南1850,北1500。但据说也可能只是战国遗址)。下面是“栎”城垣遗迹的示意图,出自许宏先生的《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原图来自刘东亚《阳翟故城的调查》(《中原文物》1991年2期)。看了这个图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各方向城墙的长度差那么多:

《桓十五年经》:
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伐郑。((p 0142)(02150010))(017)
《桓十五年传》:
冬,会于袲,谋伐郑,将纳厉公也。弗克而还。((p 0144)(02150701))(017)
我的粗译:
到这年冬天,我们的桓公与宋庄公、卫襄公、陈庄公一起在“袲”会盟,打算把郑厉公送回郑国,但没成功。
一些补充:
“袲”(chǐ)杨先生注云:“据《清一统志》,袲在今安徽省-宿县西。”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7,北纬33.7(宿州西淮北南)。
《桓十六年经》: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p 0144)(02160001))(017)
《桓十六年传》:
十六年春正月,会于曹,谋伐郑也。((p 0145)(02160101))(017)
我的粗译:
下一年春正月,四国(鲁、宋、蔡、卫,与上次会盟相比,多了蔡国,少了陈国)又在“曹”会盟,再次谋划讨伐郑国。
一些补充:
“曹”似当为“土国城漕”之曹,卫地,杨先生《闵二年传注》曰为“今河南省-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04020502),推测位置为:东经114.71,北纬35.53(滑县留固镇白马墙村)。
《桓十六年经》:
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p 0144)(02160002))(017)
《桓十六年传》:
夏,伐郑。((p 0145)(02160201))(017)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五国讨伐了郑国。
《桓十六年经》: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p 0144)(02160003))(017)
《桓十六年传》: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p 0145)(02160301))(017)
我的粗译:
到这年秋七月,我们的主上讨伐完郑国回到国内。《春秋经》中之所以记载“公至自伐郑”,是因为回来后举行了饮至之礼。
一些补充:
关于“饮至之礼”,杨伯峻先生在《桓二年传》“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处注曰:
据《左传》及《礼记曾子问》,诸侯凡朝天子,朝诸侯,或与诸侯盟会,或出师攻伐,行前应亲自祭告祢庙,或者并祭告祖庙,又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返,又应亲自祭告祖庙,并遣祝史祭告其余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舍,去声,音赦,置也。爵,古代酒杯,其形似雀,故谓之爵。爵,古雀字。设置酒杯,犹言饮酒。策,此作动词用,意即书写于简策。勋,勋劳。策勋亦可谓之书劳,襄十三年《传》“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可证。((p 0091)(02020702))
《桓十七年传》: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p 0150)(02170801))(017)
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達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p 0150)(02170802))(017)
我的粗译:
当初郑庄公曾经想让高渠弥当卿,但后来的郑昭公(当时是大子忽)讨厌此人,竭力反对,不过郑庄公不听他的。等到郑昭公再次回国当上国君,高渠弥害怕被杀,就在辛卯这天弑杀了郑昭公,改立公子亹为郑国国君。
贵族们评论说“昭公明白谁是自己的威胁”。而公子達则认为:“高伯(即高渠弥)恐怕总有一天会被杀,他报复起来太不留余地了。”
《桓十八年传》:
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p 0153)(02180201))(017)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称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p 0153)(02180202))(017)
我的粗译:
又一年秋天,齐襄公带兵来到首止,子亹(即前面的公子亹,此时为郑国国君)前往与他会见,辅佐子亹的是高渠弥。七月戊戌这天,齐人杀了子亹,还车裂了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回了子仪立为郑国国君。
这回去会见齐襄公,祭仲已经预料到不会有好结果,所以“称疾不往”。有人说:“祭仲是因为先知先觉而捡了一条命。”祭仲说:“是这么回事。”
一些补充:
“首止”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北纬34.4(今睢县城东南5公里)。
子仪之所以称郑子,是因为他还没得到周天子的正式策命,鲁国也不承认他是郑国国君。
下面是上面几处地点和一些相关地点在天地图地形图上的标注:

从图中可见,袲远在东南方向(图中右下角),离鲁、宋、卫、陈以及郑全都相去甚远,杨先生有注云:“陈立《公羊义疏》谓郑在宋、陈西,宿县在宋、陈东南,不知何以在此相会而伐郑。”四国选在此地会盟估计要多花十几二十天,多走几百里地,我也觉得确实远了点,或许是为了避寒?
《庄四年经》:
夏,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p 0163)(03040003))(017)
一些补充:
此处的郑伯乃子仪,这意味着此时周王室及各家诸侯已承认他为郑国国君,子仪一直执政了十四年(此时已执政了四年),而同时郑厉公则占据着郑国的重要城邑“栎”。
“垂”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5.53(鄄城东南十里)。
《庄十四年传》:
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请纳君。”与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而纳厉公。((p 0196)(03140201))(017)
我的粗译:
郑厉公从“栎”攻打“郑”,在大陵抓获了傅瑕,傅瑕说:“要是把我放了,我一定把主上迎回郑国。”于是郑厉公和他举行了盟誓,然后放了他。到六月甲子这天,傅瑕杀掉了郑子(子仪)及其两个儿子,迎回了郑厉公。
一些补充:
此处《左传》中称子仪为郑子,反映此段的《左传》作者已承认子仪曾实际为君,但也反映子仪最后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追赠,周天子和各家诸侯又承认了郑厉公。
“大陵”杨伯峻先生注曰:“大陵当在自密县至新郑(郑国都城)之间。旧以今临颍县东北三十五里之巨陵亭当之,非道路所经,恐不确。”我疑大陵当指郑庄公墓,正在“密县至新郑之间”,东经113.63,北纬34.46。下面是截自网上的郑庄公陵墓的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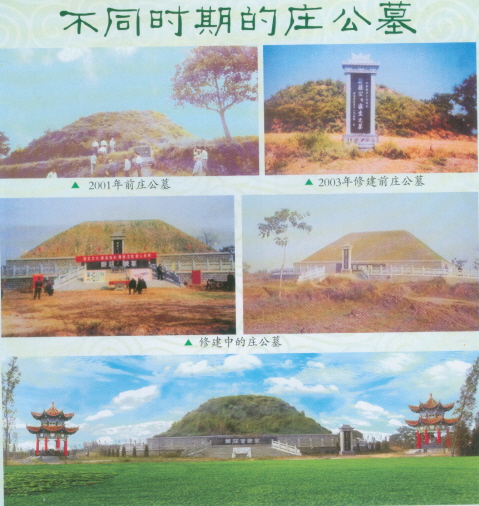
再下面是一些有关地点的天地图地形图标注,从图中可以注意到,郑国的重要城邑“虎牢”、“京”、“栎”及其都城“郑”等都在一片山区的周围,因此郑国的领地实际是以这片山区为中心的。且从栎往郑并非直接前去,而要绕行这片山区的中部,这才须经所谓“密县至新郑”的道路,估计是因为当时从山区南侧走需要跨越多条河流,还可能有湖沼,道路尚未开辟。

由于郑国的中心是山区,但其国土的重心却不在中心而在周边,山周围各城邑又不容易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当时郑国的国土就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形态,那些山周围的重要城邑更容易有独立性。当时就有人认为这容易造成“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局面,指出“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昭十一年传》(p 1327)(10111001))(108、109):
东经113.18,北纬34.85:虎牢
东经113.44,北纬34.72:京
东经113.86,北纬34.71:弊
东经113.29,北纬34.53:補
东经112.70,北纬34.50:鄔
东经113.63,北纬34.46:大陵
东经113.64,北纬34.45:鄶
东经113.71,北纬34.40:郑
东经113.47,北纬34.16:栎
《庄十四年传》: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燄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p 0196)(03140202))(017)
我的粗译:
当年(应该是庄九年)有一回在郑国的南门之中,有城里的一条大蛇和城外的一条大蛇争斗起来,结果城里的那条蛇死掉了。经过六个年头,郑厉公回到了郑国。我们鲁国的主上庄公听说此事,就问申繻说:“这是有什么妖异吗?”申繻回答说:“人害怕什么玩意儿,那东西的气势就会扩张,把人压制住。所以妖是由人引出来的,人要是自身没有痛处,妖就不会发作。人要是自己不走正道,妖就会作怪,妖就是这么来的。”
一些补充:
妖由人兴(yāo yóu rén xīng)和妖不自作(yāo bù zì zuò)应该也是成语,但不太常用。不过这里反映的思想还是很有道理的。
下面是子元(厉公)、子仪这小哥俩的合影,截自网上:

《庄十四年传》:
厉公入,遂杀傅瑕。使谓原繁曰:“傅瑕贰,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纳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吾愿与伯父图之。且寡人出,伯父无里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贰如之?苟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子仪在位,十四年矣,而谋召君者,庸非贰乎?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赂劝贰而可以济事,君其若之何?臣闻命矣。”乃缢而死。((p 0197)(03140203))(017)
我的粗译:
郑厉公回到郑国,马上杀了傅瑕。还派人对另一位大臣原繁说:“傅瑕不忠,按周天子的规矩已经伏法了。那些一心一意迎立我的人,我都应许让他们当“上大夫”,我也愿意和伯父一起治理国家。当年寡人出走在外,伯父不肯给我通消息。现在寡人回来了,伯父还不肯支持寡人的做法,寡人很不满意。”
原繁回答说:“是先君桓公任命我的先人典司宗祏。既然在这个岗位上,当社稷已经有主的时候,还惦念着外面的人,这不就是严重的不忠吗?只要有了主持社稷的人,国内之民,难道不都是他的臣子吗?作为臣子而没有二心,是上天的道理。子仪在位,十四年矣,那时候谁要是图谋迎立主上,不就是不忠吗?庄公之子犹有八人,要是他们用官爵行赂劝诱都能成事,主上怎么办?臣下已经知道主上的意思了。”于是原繁上吊自杀了。
一些补充:
郑厉公既然称原繁为伯父,而且原繁还典司宗祏,则原繁应该是郑国某位公子的后裔,不过他的先人已经典司宗祏,也就是说已经不是国君,他本人也就不是公子(从称谓而言,他多半也不是公孙)。那么,他当然就不会是郑厉公的亲伯父。
《庄十六年经》:
秋,荆伐郑。((p 0201)(03160003))(017)
《庄十六年传》:
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p 0202)(03160201))(017)
我的粗译:
郑厉公从“栎”回到了郑国,过了很长时间才报告给背后支持他的楚国。这年秋天,楚国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就因为郑厉公不按“礼”行事。
《庄十六年传》:
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p 0202)(03160301))(017)
君子谓强鉏不能卫其足。((p 0202)(03160302))(017)
我的粗译:
郑厉公又惩罚参加了雍纠之乱的人,当年九月,杀公子阏,刖强鉏。郑庄公弟弟共叔的儿子公父定叔则逃去了卫国。三年以后,郑厉公又决定让公父定叔回郑国,宣布说:“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郑厉公还专门安排公父定叔十月回郑国,说:“良月也,就盈数焉。”他的意思是这是个好月份,而且是十全十美的月份。
贵族们都说强鉏没本事,连自己的脚都保不住。
一些补充:
“刖”是当时的法定刑罚,用某种方法截去人的一段下肢使其无法行走。被“刖”以后不再能参战,就自然退出了“民”的行列。
共叔即被郑庄公“克”了的亲弟弟“段”,也是郑厉公的叔叔,此人其实在当时的郑国很有威望,《诗经郑风》中有两首诗都是专门歌颂此人的:
《郑风叔于田》: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09))
《郑风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10))
公父定叔的“氏”为“公父”,以“公父”为“氏”自然是在炫耀这一“氏”族的始祖共叔与立“氏”时的郑国国君——“公”的关系,但这个“父”并不是说共叔是郑厉公的父亲,而是说共叔是郑厉公的叔叔,当时没有现在叔叔这个称呼,现在的叔叔当时称“叔父”,属于所谓“诸父”,也就是“父”之一。至于“公叔氏”,很可能是在炫耀其始祖为当时国君的亲弟弟。
杨伯峻先生在此注曰:“古以奇数之月为忌,偶数之月为良。见顾炎武《日知录》。”“十为满数。公父定叔今年出奔,三年而复之,则是探后言之。”
————————————————————
《庄二十一年经》:
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p 0216)(03210002))(017)
《庄二十一年传》:
郑伯享王于阙(què)西辟(bì),乐备。王与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东。原伯曰:“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五月,郑厉公卒。((p 0216)(03210102))(033、017)
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p 0216)(03210104))(033、017)
《庄二十一年经》:
冬十有二月,葬郑厉公。((p 0216)(03210004))(017)
我的粗译:
郑厉公在王城正门西阙上的宫殿内宴请周惠王,让乐工演奏了上古帝王的所有音乐。周惠王赏赐给他当年周平王赐给郑武公的那块从虎牢以东开始的土地。周惠王的大臣原伯批评说:“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他是说郑厉公也照着过分的方式行事,就同样不会有好下场!这年五月,郑厉公就死掉了。
在郑厉公宴请周惠王的时候,周惠王赏给他后之鞶鑑,可是另一位在平乱中出了力的虢公请求赏赐器物,周惠王却赏给他爵。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因此而疏离了王室。
一些补充:
郑厉公之所以能宴请周惠王,是因为郑厉公刚刚帮助周王室平定了一场动乱。动乱的发动者是王子颓,王子颓就是因为让乐工为他演奏了上古帝王的所有音乐而被郑厉公看出来有机可乘。这些音乐就包括孔子听了之后“三月不知肉味”的“韶”。现在郑厉公自己也演奏所有这些音乐,这就是“效尤”了。“效”是照着做,“尤”则指过分的事。
“效尤”(xiào yóu)虽然只有两个字,但也是成语,或者会加上两个字,变为“以儆效尤”(yǐ jǐng xiào yóu),成为另一句成语,但出处还应是这里。
关于鞶鑑与爵的轻重,杨伯峻先生注曰:“爵为礼器,自贵于鞶鑑,郑文因以为小其父,而恶王。”爵的形状很奇特,下面是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一九五之“爵”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以及《春秋左传注》初版所附“爵”的图形:

就其功用而言,爵不过就是酒杯而已,但把爵造成这样奇特的形状,应该是赋予了这个“爵”某些特别的象征意义。我想,正式用到爵的场合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享宴,一类是祭祀,这在《左传》中也有反映,例如:
享宴:
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宣二年传》(p 0659)(07020303))(059)
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成三年传》(p 0816)(08030902))(069)
皆叹,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贰之有?”盈出,遍拜之。(《襄二十三年传》(p 1073)(09230301))(104)
祭祀: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桓二年传》(p 0091)(02020702))(007)
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文十八年传》(p 0630)(06180202))(062)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定八年传》(p 1568)(11081003))(128)
就上引段落杨伯峻先生注言:“舍,去声,音赦,置也。”
无论享宴还是祭祀,都是要排座次的,而且这类活动中的正式参与者每人都有一个爵,于是爵的位次就是人的座次,设置了爵的位次也就排定了人的座次。因此我想,久而久之,就出来“班爵”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指位次、座次:
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庄二十三年传》(p 0225)(03230101))(030)
事大国,无失班爵而加敬焉,礼也。(《成十八年传》(p 0913)(08181301))(083)
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襄二十六年传》(p 1111)(09260101))(095)
在位次、座次的基础上,“爵”逐渐有了特定荣誉地位的含义,但最开始恐怕还是和真的“爵”联系在一起的,《襄二十一年传》有“庄公为勇爵”((p 1063)(09210802))(090、104),似乎就真有那么个“勇爵”,就像今日的奖杯,用来奖给勇士。
因此,我猜想,此处赐给某人某个“爵”也许还意味着在王室举行的宴会上某人将要坐某个位置(班爵),或者在宗庙献祭时排某个位置(舍爵),所以郑文公才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下面是洛阳出土的一件西周爵(图片截自网上):

和虢国一样,郑国本是所谓畿内诸侯,直属于周天子,是在周王朝上有职位的,也就有义务随时为王室出力。这次周、郑分手,王室从此失去了一支可以倚仗的强大武力,郑国也丢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令箭,两败俱伤。
那么多男人为之着迷,为之丧命。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
我的理解:妇人指的是声伯之母嫁给管于奚生的女儿,即声伯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可不是"施孝叔虽然娶了管于奚的寡妇",而是娶了寡妇的女儿.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36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图版》)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49)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1)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36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图版23》)
通过以上关于鸡彝的考古材料的排比,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
其一:鸡彝的形状,无论是敞流的所谓“鬶”,还是筒流的所谓“盉”,其外形都像鸡,因此得“鸡”名。
其二:鸡彝大约产生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来在东、西方的龙山文化中开始普遍盛行。夏文化中的封口盉是从龙山文化中的卷流鬶(图版23:2)直接发展来的,到商文化中已不多见,西周已绝灭。可见它是商以前流行的器物。正因为它产生在东方,而在古代的东夷地区又曾经特别流行,因此它同时又有了“夷”名。
其三:鸡彝最早的形制为三实足,似鼎;随后又变成袋足,似鬲,都可在其下生火,用以煮液态食物或饮料。出土时有的足外有烟熏痕,内壁有水锈可以直接证明。同时它们都有流,有鋬,封口盉的顶部又开有桃形或圆角方形孔,有的陶盉上还附有小盖,这又符合了郭宝钧先生所谓“凿背纳酒,从口吐出,以灌于地”的设想,可见它又是一种灌器。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2)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其四:无论是鬶还是封口盉,都与觚或者觚、爵配套同出于墓葬,可见它们又是礼器。又因为古人迷信,常常举行祭祀时用它,所以又有了“彝”名。(《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宰鸡敬神的风习通行于近现代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之中。在古代,有用杀鸡盟誓的,例如:
《礼记曲礼下》孔疏:
盟牲所用,许慎据《韩诗》云:“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民以鸡。”
《史记晋世家》:
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月庚午,智罃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
值得注意的是,用鸡祭祀更是东方的风俗。例如:
《墨子迎敌祠》: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其牲以鸡。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
杜注:“畏其为牺牲,奉宗庙,故自残毁。”(
更有趣的是:
《说文》四上鸟部:
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鸟倝声。鲁郊以丹鸡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鲁侯之咎。”
《风俗通义》卷八《祀典》雄鸡条: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山海经》曰:“祀鬼神皆以雄鸡。”鲁郊祀常以丹鸡。
看来,用红色雄鸡祭祀乃是东方特别是鲁国地区的传统习俗。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不难从红色雄鸡联想到山东地区特别是曲阜西夏侯(《考古学报》1964:2,页75)等地所发现的大批红陶鬶了。正因为红色雄鸡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品,而红色陶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两者的关系不是再清楚没有吗?双手捧鸡曰“彝”,双手捧鬶曰“灌”,其目的都是为了祭祀。这种风习传到了西方,所以龙山文化的卷流陶鬶仍然使用红色,或近于红色的黄色。只是因为夏人“尚黑”,所以夏文化中的封口盉就改用了黑色,或者近于黑色的深灰色了(也有极少数用白色的)。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4)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标准的陶爵最早见于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只出过类似爵形器(《考古》1978:4页251,图一一:3)。然而,爵最早的形态,也是从鸡彝(即所谓“鬶”)中分化出来的。
河南登封玉村发现的一件夏文化白陶爵(韩维州,丁伯泉:《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6,页22。),就是最早的一种形制。其特点是:流狭短而上翘。无尾。无柱。流后贴两小泥饼,以加固流与口的交接处;稍晚的爵柱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体瘦长,横断面呈椭圆形,束腰,平底,有宽鋬,鋬和口唇上都有斜行划纹,象征羽毛。按其形状,与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的II式鬶非常相似,显然,玉村爵是从姚官庄一类的鬶演化来的。因为姚官庄鬶是鸡彝的一种,本像鸡,所以玉村爵也像禽类。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64)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
以上邹衡先生的论述对于“爵”的意义说得非常清楚,“爵”是作为“牺牲”的象征物使用的,在特定场合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持有。
下面的是截自网上的夏文化白陶鬶的图片,其中明显可以看到流与口交接处的“小泥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