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网站停站换新具体说明
- 按以上说明时间,延期一周至网站时间26-27左右。具体实施前两天会在此提前通知具体实施时间
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似乎要吃就得脱壳,新石器时期有石磨盘加石磨棒,应该就是配套的脱壳工具,什么时候没特别注意。
二、菜
菜是蔬菜,但那时的菜很多都不是专门种的,而是野菜。春秋那时,自然条件和现在大不相同,随处都长着各种野菜,那时人的嘴也壮,什么样的野菜都能吃。在山坡上采的,从路边沟里捞上来的,根茎叶果,生鲜腌渍,甘酸苦辛,应有尽有。其中,在我看来和现代人口味有明显差异的就是葵了。这葵不是葵花那个葵,而葵花那个葵倒是这个葵,葵花是后来传入中国的,因为葵花也像这个葵一样会随着阳光转动,所以就跟着这个葵叫了葵花。
葵的主要特点是滑,会有不少粘液,所以会滑。我想当时的食品远比现在粗砺,剌(lá)嗓子,所以人们才会喜欢上这种吃起来滑滑的冬葵。而且《礼记•内则第十二》和《周礼•天官冢宰第一》都强调说“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也是突出了滑的意义。
因为这种冬葵在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是有人工种植的,也因为冬葵可以多次收割叶子拿去吃,叶子砍掉以后还能再长出来。于是,《左传》中转引孔子的话说,“葵”因为聪明所以“能卫其足”。
《左传》中提到了不少属于“菜”这一类的食物,有:葵——冬葵,蘋——浮萍,藻——水藻,蘩——白蒿,瓠——葫芦,葑——芜青,瓜——菜瓜,菲——王瓜,昌歜——菖蒲根;
《礼记》中也提到好几样“菜”这一类食物,有:韭——韭菜,堇、荁——藜,薤——藠头;
《诗经》里更提到很多种“菜”这一类食物,有:荇菜——莕菜,卷耳——卷耳,芣苢——车前,荼、苦、苓——苣荬菜,荠——荠菜,壶、果臝——葫芦,谖草——黄花菜,莫——酸模,藚——泽泻,葽——芸苔,蓷——益母草,芩——黄芩,臺——薹草,莱——藜,蓫——羊蹄,葍——旋花,莪、蒿、蔚、萧——蒿子,芹——芹菜,蒲——香蒲,茆——莼菜,笋——竹笋。
这些“菜”大多是野菜,看来,那时的人们是把能进嘴的全都塞进了嘴里。
另据钟华-崔宗亮-袁广阔《东周时期河济地区农业生产模式初探——河南濮阳金桥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农业考古2020(04),p 020(金桥遗址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统计表),当时某地最常见的野生草类有:
狗尾草(Setaria viridis) 0.17%
禾本科 (Poaceae) 0.17%
胡枝子(Lespedeza bicolor) 0.51%
藜(Chenopodium album) 4.63%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0.51%
红鳞扁莎 (Pycreus sanguinolentus) 9.09%
异型莎草(Cyperus difformis)0.69%
眼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6.17%
麦仁珠(Galium tricorne)0.17%
牻牛儿苗(Erodium stephanianum)0.17%
茴茴蒜(Ranunculus chinensis)0.17%
苘麻(Abutilon theophrasti)0.17%
地肤(Kochia scoparia)0.17%
苍耳(Xanthium sibiricum)5.15%
与上面同类的结果还有不少,在此只是拈出一例展示而已。
前面也提到过,当时的人食谱中有这么多种“菜”,也是因为当时人常常会遇到粮食不够吃的时候,于是就需要瓜菜代,赶上荒年,这种瓜菜代就更频繁,所以,就有了形容这时人们脸色的那个成语,叫“面有菜色”。
因此这“菜”和我们现在的意义不一样,什么下来了吃什么,瓜菜半年粮,饱腹的作用更大些,万一“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僖二十六年传》(p 0439)(05260302)),那就真没活路了。
三、肉
我们的先人老早就不再以肉食为主了,到春秋时,已经是“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玉藻第十三》),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吃上一顿肉的。
据认为,“以粟和黍的栽培、猪和狗的饲养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业经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腹地先民主要的生计方式”(《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史前生业经济复杂化的启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为例》,《华夏考古》,2017(4)),随后,中原地区从不同的方向引入了小麦和水稻,接着,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中原地区又引入了牛羊。
于是到春秋时代,肉食便主要是五畜:“牛、羊、豕、鸡、狗”,大牲畜是牛羊猪,狗是补充,家养的禽类除了鸡还有鹅之类以及禽蛋;另外,还有各种野味作为调剂:雉、鷃、鹑、鹜、凫、雁、莎鸡、兔、貆、鹿、麕、麋、豝、豵、兕、熊、罴、猫、虎、豹等;包括水边上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类:鲂、鳣、鲔、鳏、鱮、鲤、鳟、鲿、鲨、鳢、鰋、鲔、鲦、鳖、蜃、蛤、鼋等。
牛羊虽然是外来家畜,但到了春秋时代,也已经引进了上千年。不过牛羊是通过北方草原地带引入的,当时中原地区还有混居的戎狄,也有着北方草原的背景,他们和华夏族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语言文化都不相同,在饮食方面华夏族虽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特征,一般的肉食仍主要是猪肉。《礼记•王制第五》中也提到“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正反映在牛、羊、猪这三种大牲畜中,猪是最普通的,而且和狗一样,也是比较低级的肉食来源。
在进行祭祀时,用到三种大牲畜牛猪羊的叫做太牢,是最高等级的祭祀,如果节约点单用一头猪一只羊就是少牢。用牛作祭祀大概是商人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就是养牛贩牛的,而且他们祭祀时可不像春秋时代周人那么抠抠搜搜,他们一次祭祀会用上百头牛。这可能也反映商人和周人生计的不同。
又据认为,“2500BC前后,先民将牛和羊引入中原地区,并创建了与猪、狗不同的饲养方式,即以旱作农业的副产品 (茎、秆、叶等) 喂食牛,以野生植物放养羊。”(《先商文化时期家畜饲养方式初探》,《华夏考古》,2013(2)。)。总之,由于这三种大牲畜的食性不同,对他们的饲养方式也不一样。这其中,猪是最纯粹的肉食提供者,而牛可能用于耕作乃至驾车,牛皮和牛骨还是手工业的原料,羊则还可用到皮毛。
据后世的经验,大量放牛和大量放羊不太一样,需要更好的自然环境,或者说,只有适于种地的地方才适于放牛。实际上,在春秋时代,这样的地方正逐步被农田挤占,畜牧族群的生活空间正一步步丧失。
当时在中原还有从事畜牧的戎狄与华夏族群混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其生业与华夏族群恐怕还是有区别的,他们的食谱大概也和华夏族群不同,吃牛羊肉吃得更多,不过他们正逐渐转而从事农耕业。
而某些生活在农牧业分界线北侧的华夏族群,很可能也入乡随俗,以畜牧为生业。或者说,其实他们的生业是谷子种植加畜牧,谷子种植对降水量要求没那么高,同时从事畜牧业又能利用谷子的秸秆,这是远古传下来的成功生业模式。对他们来说,也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吧。当然这些华夏族群可能只是上层,聚族而居的、承担大部分生产活动的下层可能本来就是畜牧族群。而在这种模式下,高低贵贱并非以肉食者与非肉食者来区分的,也许是通过食用肉的不同部位来区分。
除了家养动物,还会有少量猎杀的野生动物,作为肉食的补充,但占比有限。
例如,据刘欢《甘肃天水毛家坪遗址动物遗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p 137、140,当时在今甘肃一带两个遗址考古发掘所得秦人的肉食量比例(百分数%)分别推测为:狗8.56、5.69,猪36.67、25.58,羊7.05、2.84,黄牛27.71、31.27,马12.29、17.05,鹿类6.24、15.40,其他野生动物1.18、2.27。
四、果
果是水果,准确点说,应该是既有水果也有干果,现在有个说水果的绕口令,最后一句是“苹果桃子柿子石榴李子栗子梨”,也包括了干果栗子。
当时最常见的水果是枣,最常见的干果是榛子和栗子,《左传》、《礼记》、《诗经》都提到过。《左传》、《礼记》、《诗经》都提到过的还有一种也属于果类的,当时叫椇,现在有些地方叫拐枣,其实这种拐枣可吃的部分既不是种子也不是果实,而是果柄,也因此改进的余地不大,今天已经没太多人再吃了。但也反过来说明当时的水果远不能和现在的比。
然后就是甜瓜类,这个也算是水果,非常常见,江西-靖安-春秋大墓数十名死者最后一餐吃的就是甜瓜。
还有现在常见的桃,李,梅,杏,楂,梨,以及郁李等蔷薇科水果,虽然好看又漂亮,但那时不一定十分好吃,大概和拐枣差不多。那时的果树栽培技术还不十分成熟,水果保存也不易,这些水果也就没有今天那么流行。《诗经》中还提到猕猴桃,柿子,木瓜,还有山葡萄,以及偏门的桑葚,和前面几种蔷薇科水果也类似。
《禹贡》里还提到当时的扬州(长江中下游)出产橘、桔、柚这些南方水果,屈老先生说是“后皇嘉树”,而且“受命不迁”,于是橘生淮北变枳,这一类水果就没能在中原一带生根。
五、酒
酒这东西,流行的高峰绝不是春秋时代,而是出了酒池肉林传说的商代,商代礼仪以酒为中心,所以在商代礼器中,酒器占有重要地位,与周代以食器为主的礼器组合大相径庭。
但是春秋时代的酒,还是有着丰富的品种,从原料上看,黍、粱、稻、麦都可以酿酒,还有用稀粥作为酿酒原料的(酏),从品种上说,有一般的酒,也有甜酒酿(醴),还有加了香料的酒(鬯),也会经过过滤得到所谓“清酒”。
那时的酿酒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提出了一直流传至今的六必:“秫稻必齐,曲蘗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这六项原则(《礼记•月令第六》),但是那时还没有蒸馏酒,据认为蒸馏酒的出现要到西汉。
有一种特别的酒——秬鬯,是加了香草调味的酒,也是周天子赏赐霸主的标配,和“虎贲三百人”什么的并列,传到后世,还成为“九锡”的一种,更是御酒的老祖宗。
那时的贵族在日常宴饮中也少不了酒,《左传》中就多次提到酒,其中有酒醉误事的,有撒酒疯的,也有在酒席上生事的,以及在酒席上成事的,又有在酒席上起事的,酒一直是贵族重要的社交媒介,也是贵族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六、油
油是指油脂,按来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油料作物,当时其实是混在五谷或六谷里作为谷物的,主要又分两种,一种是大豆,当时叫菽,一种是麻籽,当时就叫麻。再一类就是动物油脂,当时叫脂。
大豆和大麻,似乎在四五千年前就有种植,前者可以改良土壤,后者则还是纤维的来源,但到后来,油料作物和纤维原料作物大概会分化。
至于动物油脂,只能是吃什么肉就会有什么动物的油脂,同时,这些油脂还会用在车轴的润滑等方面。
另外,各种油脂还是照明的燃料。
七、调
调是指调味料,春秋时代的人讲五味,杨伯峻先生认为是“辛、酸、咸、苦、甘”,杜预则说是“酸、咸、辛、苦、甘”,顺序不同,五味则完全相同。
不过要调出这五种味道,那时的人所用的调料和我们现在的调料还是不完全一致的。
先说咸,这一样古今一致,都是用盐,那时的盐应该已经足够精细了,在比较隆重宴席上,还会摆出塑成老虎模样的一大块盐,以示郑重。不过这种摆放盐老虎的方式,恐怕也表明那时盐的珍稀,是可以显摆的。
再说酸,当时已经有了醋,是酒酿酸了的副产品,但是口味似乎不算好,于是还有一种当时常用的酸味调味料,就是梅子,梅还和盐一起成为调和鼎鼐的象征。这种调味料一直到三国还在流行,所以才有望梅止渴。
然后是甘,那时还没有蔗糖,所以甘并不等于现在的甜。那时的甜味调味料是饴糖,是从粮食中提炼出来的,融化了之后是膏状,很粘,所以可以堵灶王爷的嘴;冷却后还挺硬的,所以要零敲牛皮糖。除了饴糖,提供甜味的还有蜂蜜,大概不像饴糖那么普遍。
还有辛,大体等于今天的辣,那时没有辣椒,辣味调味料一是蓼类植物,一是葱姜椒芥,总之没有辣椒的辣味正。
至于苦,自然界中味苦的野菜还是很多的,有的就直接被称为苦。
除了五味,也有各种特殊风味,还会用到胡椒、桂、薤之类、乃至各种水果。
当然,我们不能忘了鲜味的调味料,现代在这方面有了味精,但食不厌精的古代贵族有办法,他们会制作各种风味的肉酱,用来调出各种不同的鲜味,麻烦是麻烦了点,可我们现在那些讲究的人不也是不用味精了吗。至于用什么,那就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了。
————————————————————
那时吃东西还经常用手,据说以右手为主,而从染指于鼎那个事件来看,用手也已经有一定的限制。而且那时还有了筷子,叫“梜”,也叫“箸”。不过那时筷子在人们手上还不像现在这样无所不能,还被限制“饭黍毋以箸”(《礼记•曲礼上第一》),只是“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礼记•曲礼上第一》)而已。当然,那时还有各种其他进食工具,好比“匕”,前头有尖,边上有刃,中间有弯,像刀又像勺,能切能刺也能舀。
那时舀水和喝水已经有了葫芦瓢,这也是一直传承到现代的日常用具,配套的应该有陶制的水缸吧,当时造不出大的,中的小的总该有的,日常用水总不该是现用现打。
而一般人吃饭的家伙,可能有陶器,甚至有竹编或藤编的器具——好比箪,在《左传》中还提到过用囊装食品,可见当时的食品很多不是连汤带水的,好比“糇”——饭团,无论是竹筐还是布囊,都能盛。又好比“束脩”——干肉,不过这大概得孔子那样的高级贵族才能常吃的。
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论语•雍也第六》),大概是那时下层“民”吃东西的常态吧。
当然,也不能少了一只常年架在灶上的陶鬲或陶鼎,其中总是煮着一锅老汤,什么东西都煮,丰俭由人。
至于贵族,规矩很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第十》),钟鸣鼎食,折冲樽俎,对于他们,吃就不仅是糊口饱腹而已,而这,也和我们的主题关系不大了……
水稻不清楚,北方早期的主食是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不脱壳就没法吃。早期脱壳,最简单的就是把谷粒放在石磨盘上,用根石棒反复擀,之后吹去外壳,剩下的就是米粒。做粥和饭的时候,再简单的淘洗即可。
再到后面,就有了碓,一个大石槽,谷子放坑里,用杵来舂捣。
再到后面,有用脚踩的碓。和上面的杵臼一样,只不过用了杠杠原理。
大概秦汉的时候,石磨应该也比较成熟了。
在中国,水稻是原产,历史近万年。小麦是舶来品,进入中原已经是龙山时代,真正普及已经是夏商以后,而且长期排在粟和黍后面。主要是不好种而且不好吃。不好种是因为不符合古人的种植习惯,这玩意得立冬种,夏天收,跟古人春种秋收的认知不一致。不好吃是,中国没有粉食习惯。中国的传统,是粒食。不论水稻、小米还是黄米,要么做粥,要么做饭,都是完整的颗粒。小麦西来,中国本土居民肯定也是按照小米大米的方法烹调,可小麦无论做粥还是做卖饭,都不好吃。
西汉以后,石磨普及,炼丹术流行,带来两个突变。一个是大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豆浆豆腐以及进一步的深加工产品才有了可能。
另一个,终于可以吃饼了。以前面食都叫饼,水跟面合并就叫饼。煮面条就叫汤饼,蒸馒头叫炊饼。到南本朝时期,发酵技术出现,终于馒头出现了。这样我们对于小麦的烹调方式才真正的成熟,这都已经是隋唐了。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小麦作为舶来品,只是传来了种子,但烹调方面没传过来。所以中东一带烤面包的技术,中国一直没有。而是利用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蒸这种方法,创造了包子和馒头这种饮食,对应西方的烤面包。
学长勿怪。
我认为春秋时期华夏大地上存在各种族的氏族部落和不同发展水平的政权形式,不能仅以华夏族和犬戎族这两个概念加以说明。
周早期是今天陕西地方的周人,东向出击制服河南地区的殷人。这是当时主要的种族矛盾。东部的殷人之下,还有被商汤征服的夏人,及其他种族如东夷人。在河南山西一带有犬戎。
我认为所有这些曾经在华夏大地上生存的种族经过互相征服和同化,才有今天的华夏族的祖先。
这个陈述可能不准确。
粒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最直接方便,除去壳外无需额外加工。与时代的技术和工具相关。
各种谷物都可以被磨成粉深加工出其他形式的主食。如今天南方常见的米粉年糕之类。北方山东的小米面煎饼,河北的糜子(一种粘小米)面“挪挪”(当地土音)。
麦粒直接煮熟食用也很好吃。口感比米粒更要劲道有力。只不过这样吃的不多。上世纪时山东临沂还有一个古代流传下来的“糁”,即鸡肉汤煮麦粒。不知现在是否还有。
但如果从种族角度研究,困难比较大,无论是从所谓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就是量头盖骨之类,还是测DNA,还没有足够详细且对应各个族群的资料,尤其是上层与下层还可能不属同一种族。
总而言之,难!
粒食着两个字就是直接从文献来的。
虽然,但确实不够准确,您说得有道理,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不得已。
而麦粒好吃不好吃我是听赵先生在电视里说的,我没吃过,这是依附权威吧。似乎只能如此。
更彻底的方法是自己煮了尝一尝,但还有不同烹饪方法的问题。
总而言之,表述还可以再模糊一点,也能更准确一些。

就是这种,抖音里看到过,非洲还有部落用这个碾粉,抖音里那个做工比这个差的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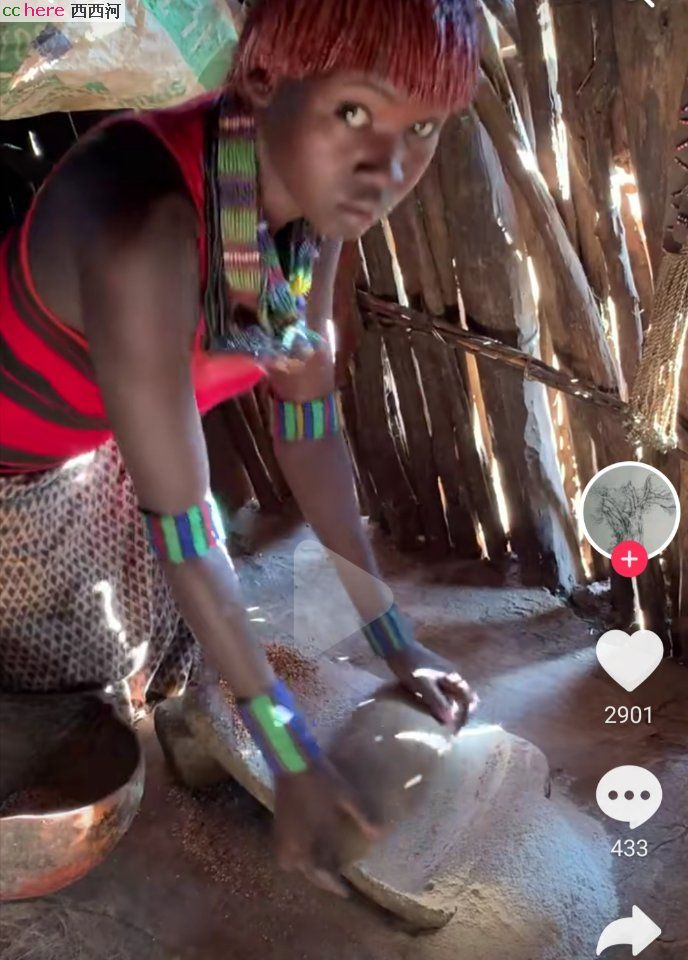
糁这个字,字典里叫“san(三声)”,当地人叫“sa(四声)”,是当地特色,不过作为外地人,有点喝不惯。
首先是华夏这一概念:
其次是为什么像一个族群:
也就是说,不管是华夏还是中国,自始至终是一种由文化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内部存在不同水平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古今都会认为南北朝是外族,但和今天的语境有所不同。依然是以文明为进退。
但是宋明时期的发展使得华夏接近现代的民族。虽然文化为重,但已明显区分夷狄。
但是明亡使人很难再坚持这种正统的意义。
这也就重新回到以文明发展为标准的华夷关系。
换句话说,华夏,一直就是「文明」的意思。尽管中间与国家、地区有所捆绑,但始终不脱离文化成分。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在于,这就无法简单使用现代种族观念进行判断。尤其是血缘。进而,似乎找不到一个什么好的符号来表明这点。用部落也会因为与原始或者非洲有情感联系而变得不合适。
所以直接把族这个字删掉就可以了。
“另外,“麦”——“麥”这个字一直有学者认为是出自“來”——“来”这个字,但仔细想来,应该是“來”——“来”这个字出自“麦”——“麥”这个字:”。。。很有鸡生蛋,蛋生鸡的神韵啊。。
倒是暴露了他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西亚种小麦是粉食,就是烤面包。逻辑自相矛盾点,就是东传只传了种子,没传吃法。
还有就是看不懂后面三幅图,云遮雾罩、忽忽悠悠的,到底出土的是种子粒数?还是换算重量?为什么27份要和4份排在一起比概率?
如果认为华夏只是代表文明,不认为是族群的话,那汉朝之前中原居民是什么族群?很明显这些居民已经形成了与周边民族区别明显的民族共同体,正是这个民族共同体,才使得秦汉帝国成为可能
这个族群不适合称为周人,因为宋国、楚国这些跻身于主流诸侯国之列的居民不是周人。
那问题来了,还有什么比“华夏族”更适合呢?
没说秦汉如此。华夷一直都是政治秩序的符号,只是表达了结构。有夷必有华,有华必有夷。(有趣的是中古神话也是如此,越接近中心越有秩序)
如果说民族,首先要界定民族的概念,而这很难达成一致。因为中国是例外最多的国家,比如远人可能是原先周人的后裔,某族可能由汉人和夷人组成,某夷可能通过入主和界定自称。
即便是个人认为最合适的说法,也就是斯大林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对古代中国也很难说,因为语言难通、多语系(同文),地域一直变化,经济生活是朝贡体系外独立,民族多样化……甚至政治体系都可能是多元的(一国两制古已有之)。共同心理素质就更难说了。如果加上最常见的人种族裔,那就更不可能了。
然后我们可以考察华夏族这个概念能用来统摄什么?是一个时期、一定疆域、一些族群、一个中心文化所组成共同体中成员的自我指称。如果与现代中国以外的人区分,意义很大。但如果是内部指称,不用也没问题。完全可以使用他们各个时期具体界定的指称,不管是他人给予的,还是自我定义的,直到进入某种结构,消解自身。而且直接用朝代、胡汉之类都没什么问题。
回到层主的问题,这个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或许现代可以称之为民族,但实际上很少有人通过这个方式表达。虽然古代有类似说法,但不过是为了命名方便,随着具体情况变动。就像对地域从属的指称,原本的六国的说法甚至延续到西汉后期。而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定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本质的那个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现在文明的说法会出现问题,是因为原本的天下消失了,变成了世界。从一个文明,变成了多个文明。但是文中指的是先秦时期,有明确的限定,问题不大。而且那个时候也很难说是民族概念。即便是有所接近。